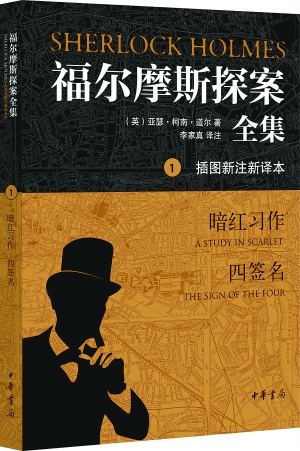
福尔摩斯新版封面

1916年版封面
11月15日,中华书局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新译本将与读者见面,而这距离中华书局首次引进福尔摩斯全集已过了整整96年。有趣的是,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的中国首部福尔摩斯全集,大侦探福尔摩斯说的是地道文言文,因此,有网友希望最新的福尔摩斯全集可以再度回归,让福尔摩斯仍开口说“文言文”。
但福尔摩斯真的还能再说文言文吗,随着新版的即将面世,谜底也将揭开。
首版“福尔摩斯”成“纪念册”
中华书局新版福尔摩斯全集为全七册,即《暗红习作·四签名》、《福尔摩斯冒险史》、《福尔摩斯回忆录》、《福尔摩斯归来记》、《巴斯克维尔的猎犬·恐怖谷》、《福尔摩斯谢幕演出》、《福尔摩斯旧案钞》。新版不仅对此前面世多个译本的错谬之处多有纠正,尤具收藏价值的是,书中还有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的《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》仿真本一册和19世纪伦敦街道地图一份。
颇具悬念的是,1916年版福尔摩斯全集此前还被珍藏在中华书局图书馆,而且只剩下孤零零的一套了,一次偶然的机会才成就了此次与读者的最新碰面。中华书局大众出版分社社长宋志军说,今年是中华书局成立百年,在整理百年总书目的时候,发现了1916年版福尔摩斯全集,“恰在这时,原《英语学习》副主编李家真说了一句话:‘说起来,中国的福尔摩斯全集中华书局是第一个出的。’”
随后,在中华书局图书馆里,宋志军找到了最古老的福尔摩斯全集中文版。“封面是牛皮纸颜色,上面还有手绘图。全集共有12本,但封面稍有破损。”出版社相关负责人最后一合计,为什么不把老版和新版合集推出,这多具有独特的纪念意义。“其他福尔摩斯全集都是附赠地图、烟斗、明信片,但这些年从来没有出过文言文版。”宋志军说,因为原书中有些字已经不太清晰了,因此,此次选了第一册制作成仿真本,让读者重温说文言文的福尔摩斯的独特感受。
民国文坛大家首译文言文
对于中华书局的出版人和读者来说,和1916年版《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》一同发掘出来的还有珍藏已久的出版往事。后来成为“侦探小说泰斗”的程小青,以及“鸳鸯蝴蝶派”作家周瘦鹃、严独鹤、陈小蝶和天虚我生等人,几乎都是民国时期的文坛大家,是他们用浅显的文言文,首次让福尔摩斯说起了中国话。
据中华书局考证,柯南·道尔写作的福尔摩斯探案故事,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(1887年)在英国陆续出版后,不久即被译成中文。1896年,《时务报》首次连载四篇福尔摩斯探案故事,得到中国读者的热烈欢迎。民国建立后,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的中文翻译引进,几乎与欧美同步。民国五年(1916年)五月,成立仅四年多的中华书局率先推出《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》,这正是福尔摩斯探案故事第一个中文全集,共收录福尔摩斯探案故事四十四篇。
尤其难得的是,全集体例完备,有凡例,有包天笑、冷血和严独鹤撰写的序言,有五四新文学运动健将刘半农为作者柯南·道尔作的小传和为全集写的跋文。从序文中还不难看出,出版者实有“喻教育于小说”的良苦用心,如包天笑序所说“必其人重道德有学问,方能藉之以维持法律,保障人权,以为国家人民之利”,其实是点明了做侦探的条件,而冷血序言和严独鹤序言则直指中国官府侦探之腐败,提出发展“私家侦探”的主张。全集推出后大受欢迎,三个月后即再版,其后不断重印。
关于福尔摩斯文言文版的神韵,一位名叫“芥末花花”的网友评论说:“白话文好懂,但文言文自有其妙处,确有另一番滋味。”这位网友还以《呵尔唔斯缉案被戕》的开头为例:“余友呵尔唔斯,夙具伟才,余已备志简端,惜措词猥芜,未合撰述体例。兹余振笔记最后一事,余心兹戚。盖自第一章巧验红色案起,至获水师条约案止,即欲辍笔,不复述最后之一事,诚以提论此事,使余哀怆。时逾两纪,犹未慊也。”“芥末花花”还笑称,看完文言文版的一些故事,“忽觉得福尔摩斯很像是个丐帮帮主,屡屡在关键时寻一群流浪小儿帮忙打探消息。”
用文言文翻译书中新闻报道
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最新版的译者、今年40岁的李家真酷爱“文言文”,他喜欢中国的文言文,也喜欢福尔摩斯所处的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文,他认为那时候的英文更优雅、更含蓄。但李家真说,相较于古代英文,中国文言文还是更优美。
从去年3月至今年4月,李家真沉浸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文和中国文言文奇妙交汇的世界中,早上8点至晚上8点是他的翻译时间,而晚8点以后,他喜欢阅读。“我怕自己过于沉浸在英文环境里,容易丧失掉对中文的感觉,每天都看中国古代诗词、还有古代笔记之类的书。”
李家真发挥了他的特长,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中反映的时代大致相当于中国的晚清时期,为给读者增加时代氛围,李家真在翻译小说中引用报纸报道时,特别采用文言文进行翻译。“但我用的是浅易的文言文,因为这是一部侦探小说,如果度把握不好,会对读者了解案情产生障碍。”
李家真算了一下,从中华书局首出的《福尔摩斯侦探案全集》中译本开始,到他这一代已是第四代翻译了。他坦言,和前几代翻译相比,互联网的便捷和海量优势,以及出国的便利,让他寻找资料更容易,也让他为翻译细节能找到更多的可靠依据。
“‘福尔摩斯’中文版的主流译本我都看过,但还是发现不少问题。”李家真说,像1916年首版的第一册《血书》翻译严谨,但因为时代的局限,也难免一些错误,译者周瘦鹃就把“神圣法庭同盟”,翻译成了一桩案子。而关于“神圣法庭同盟”,李家真在网上进行了海量搜索后方找到了准确译法。
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家居装置,竟然和李家真儿时有相同之处,这也是有趣的一大发现。李家真的家乡在四川内江,在他幼年时,当地有用窗板加固窗户的习惯,而百年前的英国竟如出一辙。“有些译本,往往就是类似细节有失真之处,它们一般将‘窗板’翻译成‘窗帘’。”李家真认为,细节的失真,不能真正反映那个时代,因此他花费了很多工夫抠细节。
(编辑:黄奥)
